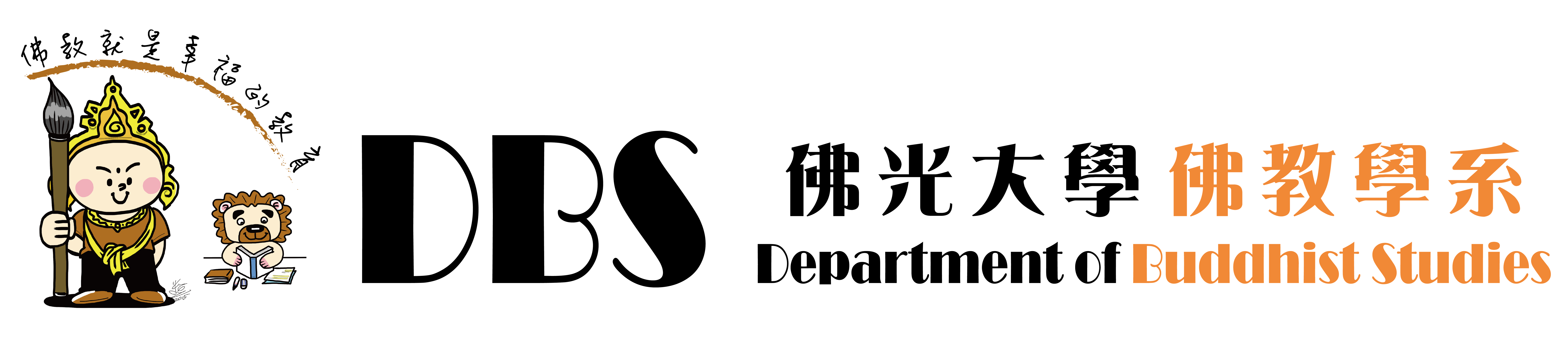(佛光大學佛教學系研究生學會/礁溪報導)信仰與學術研究能否平衡?高明道教授應佛光大學佛教學系研究生學會「雲水小參」講座之邀,於2022年3月8日雲水軒,分享對「宗教信仰與宗教研究」的看法,為此論題帶入跨宗教比較的視野,提出佛教信仰與學術研究並不衝突的理由。研學會也特邀陳一標教授為講座擔任引言。吸引約八十名學、碩、博士生前來聆聽。
高老師首先帶我們生動地分析漢字。「信仰」常與「奉」的意象相連,有向上尊仰、雙手朝上供奉的意味;「研究」意味探討,從聲符「罙」以及「究」此字的意涵來看,則有向下深入、徹底的意味。作為信仰與研究對象的「宗教」一詞非中國本有,是日本人在明治維新時效法西方大學制度,取自身文化裡有的「宗」與「教」二字──當然這些也來自佛教用語——相結合,以對譯religion學科。中國文化固有將宗、教二字分開使用的文化,「教」的古老字形還清楚呈現孩「子」被一隻「手」持「棍」教訓的樣子,此外也有思想體系之意。
在六道,人道特別有「信仰」與「學術研究」的活動現象,但「信仰」者泛,從事「學術研究」者少,這與果報有關。人類容易有信仰,可能因此走上歧路,也可能為此帶來社會人我和諧。學術研究則需長遠投入精力時間才看得到成果,它對謀生而言並非必需。此外還有一種向度座落在這兩極間,即神職人員或出家人對教義、儀軌等作的「研究」,是教團內部活動,與需接受公開批評的學術研究有所不同。
「信仰與學術研究之間,有無矛盾?」高老師娓娓道來親身遇過的基督宗教、佛教信徒,面對兩相衝突時的種種態度——
約三十年前,有瑞士的神學家在臺灣演講,引經據典直明這個宗教不應傳教,「我當時在想,底下的傳教士們聽了今晚要怎麼睡呢?」教會甚至禁止他在大學教神學。當他要往生時,還拒絕採用該教儀式。但是他卻從未退出教會。
有一位德國人在大學是讀基督教神學,他說,虔信的學生讀神學系,往往面臨所學與信仰的劇烈衝突。他畢業後因對基督教團體失望,轉而信佛。後來推薦他住在臺灣的道場進行田野研究,多年後輾轉得知他對佛教失去信心而消沈。「他一直追尋信仰歸宿,如今問題出在信仰,還是研究呢?」
還有一位精通西藏學的德國學者跟他說,由於了解西藏,所以難以學西藏佛教,於是改學禪。但當看有關禪宗研究的書時,又認為:「這個不能看,再看下去就無法修禪。」原因是禪宗歷史有杜撰色彩。
所以,信仰與學術研究能否平衡?「在我看來,如果你信仰的是佛陀的教法,可以找到平衡。」這是因為,佛教不是一神教,而後者將信仰建立在不容檢證的「神的話語」之聖典上,導致至今不乏有因聖典翻譯錯誤導致信仰偏離原始教導的事例,神學家往往要冒著生命危險來指出其非。
相對的,佛陀教導信徒要聞「思」修,而非聞「信」修,即要以「思」來反省所學,是將教法內化的必要過程。但在佛教所流布的一些文化傳統裡,卻沒有講究「思」的重要。
巴利注解書就清楚說明,「聞」來的知識都是師父的東西;「思」是經過一番苦工去考察、整理,得來的一半是自己的,一半是師父的;「修」的結果則全是自己的了。「『思』就像安全網,讓我們在信仰裡,面對分歧的文化現象時得免於迷失。」而學術研究其實無異於此,都要認真、扎實,追求破除無明,努力看出生命輪迴或問題的癥結。
在最後問答,陳老師向高老師請益:當聞思修,在「思」的過程也會遇到經典教義或宗派解釋間的矛盾問題,例如:唯識學主張有一類眾生無法成佛,但華嚴宗、天臺宗等則持相左立場;又比如,當以三乘為究竟,還是以人人都可成佛的一佛乘為究竟?
對此,高老師分享他的看法。站在佛法都是應機應時、為了利益眾生而施設的立場,認為諸如「一闡提不能成佛」這類說法其實有著激勵眾生努力證明自己並非這類根性、進而奮發修道的效果,這正如有的基督教徒會為了證明自己不是排除在「上帝的選民」之外而努力精進。再者,有關三乘,其中「辟支佛」並非佛陀所教的修道目標之一,而是出自印度其他宗教的東西;至於三乘與一乘這種形而上的問題,可以在學術研究上加以研討,但應不構成生命實踐、輪迴與解脫上的切膚問題;菩薩道與聲聞道有很多共通點。
「譬如一個人發高燒,醫生告誡要多休息;痊癒後伴隨肥胖,醫生告誡他要多運動。這看似矛盾,但醫生並非從頭到尾都要人運動,或從頭到尾都要人休息。」高老師指出佛法應機應時的特性,當出現矛盾時,不是佛法的問題,而是翻譯、傳承等文化問題,導致種種流變、差異。
最後,以一位在巴利傳統出家的友人為例,「他精通巴利語,也曾指出巴利的傳統是有些問題的。他自己發願:只要幾個小時打坐,就要花幾個小時從事學術研究;幾個小時研究,就要花幾個小時打坐。從事學術研究,是為了回饋眾生。」為佛教的學術研究不與信仰衝突的論題,陳出深具啟發性的一例。